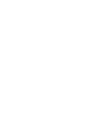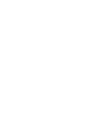洁身自爱 - 第17章
世事总是教她在无从选择的选项里做出选择:母亲去世了,司澄和她分了手,她不得不来到巴西,又不得不从隆多尼亚州调到阿贝特河。
高洁闭上眼睛,“我??相信你。你尽管??去做。”
“如果,出了意外,怎么办?”于直问。
高洁将眼睛睁开,盯牢眼前的男人,她一字一顿说:“不,怪,你。”
于直跪伏下来,一手提起高洁的手臂,保持着平衡,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,对准了位置。
接下来的动作会令这个女孩疼痛难忍,也许会再次晕过去。他提醒她,“会很疼。”他听见了她咬牙的声音。
当于直将高洁的手臂推回去时,她的身体随之僵硬地弓起,继又痉挛着抽动,牙关咯咯作响。
他说:“你忍不住可以叫出来。”
但是高洁没有,她咬到了自己的唇肉,血腥味冲进食道,她忍不住吐了出来。
又有人走了进来,高洁不知道是谁,只模糊听见有人用英语在问:“上帝!她居然忍住了,她居然没有尖叫。她会好起来吧?”
又有一个人在用英语说:“灌她阿司匹林。于,给你绷带。固定住肩膀,帮她减轻疼痛。”
她被撬开口腔,被灌下水和药片,他们拍她的背心,帮助她吞咽下去。然后她的手臂被固定住,袖管被剪开,手肘和肩膀被人用绷带绑好。有个人一直拖着她的背脊,还在用湿润的帕子擦拭她的额头她的脸,额前冰凉的触感,温柔的动作,就像小时候病重时,母亲所做的那样。
她下意识地,辗转着用脸颊去靠近那掌心的温度,宠物一样冀求着掌心展开,抚慰住她的疼痛。
又不知过了多久,高洁再度清醒过来时,发现仍躺在船舱中,身体的疼痛已经减轻太多,这令她舒服了不少,精神也恢复了一些。
船舱内依旧无人,只空空吊着四只吊床,随着船身波动微微摇晃。船舱一角堆放着一堆行李和器械,高洁看到其中有两台摄像机。
她突然想起来她刚才应该呕吐了,虽然身边没有呕吐物的痕迹,但是身上有酸馊难闻的气味。
死生大事渡过以后,个人的羞耻感席卷而来。高洁知道自己的身体又脏又臭,比自己不能动弹的左臂更让她难受。
她躺着睁着眼睛发着愁。这是有生以来从未遭遇过的困境。她在犹豫是不是呼唤于直。
念头一起,于直就推开门再度走进来,手上端着一个大碗。
“我想你应该醒了。饿了吗?”
他蹲下来,高洁挪动身体往旁边退了退。
于直笑起来,一眼洞穿她的心思,“想洗澡?”
高洁张了张嘴,声音沙哑得自己都认不出来,“有女人吗?”
于直像个恶作剧的男孩一样,把头略歪一歪,勾着唇角,“没有。”
高洁咬一咬唇,咬到唇上的伤口,疼得抽气,她又问:“多久能靠岸?”
“我们在阿贝特上游遇到印第安人和矿工的争斗,被当做同党也被印第安人伏击了,为了避开正面冲突区域,就近躲进一条支流,在河里捡到了你。现在——”于直顿了顿。
高洁微微抬头,把嘶哑的嗓子扯高了三度,“迷路了?”
于直撇嘴,“我们没这么无能,只是绕了路,要回到离这里最近的港口恐怕得多花上一周。”
高洁把后脑勺无力地垂到枕头上,轻微地叹了口气。
“我们的向导告诉我,往前再驶半个小时,可以靠岸休整,岸上有瀑布可以洗澡。”于直用根本不掩饰的笑意望住高洁。
高洁抬起眼睛瞅他一眼,他真心实意地用表情表达了他的不怀好意和幸灾乐祸。
她想了想,又想了想,下定了决心,“我需要洗澡,我也需要一套新的衣服。”
于直摸了摸下巴,高洁才注意到他和初见时不太一样了,比那时候黑了,或许是因为在野外不及打理,蓄了些短须,头发也长长了,用女用发夹将刘海全部夹在头顶,在脑后扎了个小鬏,露出宽阔光洁的额头。
成熟男人的气息,就在她的面前,比自己的脏和臭更让她难堪的,是男性的荷尔蒙,无时不刻地挑逗。
他偏偏还在利用现在的优势,“船上有四个男人,我,我的美国导演,我的加拿大摄影师,我临时请的巴西向导。你准备挑谁帮助你呢?”
高洁吐出一口气,狠狠瞪住于直,“你!”
于直愉快地拍拍她的头顶心,就像夸赞自己的宠物一样。他说:“好选择。现在,为了你等一会儿有力气下船,吃点儿?”
他拿过靠垫,帮助高洁半坐起来,高洁动一动自己尚能活动的右手,“我自己来。”
于直没有再同她抬杠,将勺子塞入她的右手,端着碗坐在她的身边,充当她的人肉桌板。
吃饭片刻,这艘小驳船上的其他人员陆续进来同高洁打招呼。
于直对她没有任何欺骗,他的确是带了一支很正经的纪录片拍摄团队,如他所说,一个美国导演、一个加拿大摄影、一个巴西向导。美国导演告诉高洁,他们还有三个摄像在另一处雨林补拍镜头。
高洁毫不客气地将于直的手臂当做桌板,一勺一勺慢悠悠舀着那碗里的汤饭吃。汤饭不知是他们之中谁做的,但是用肉骨头汤泡米饭这样的做法,也就只有中国人会做。她发现汤饭口味不错,温度适合,没有对她口腔内的伤口造成伤害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