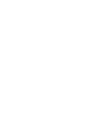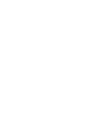牧野流星 - 第十六回世难言徒自苦情怀愁锁倍堪
杨华深入柴达木山区,放眼是一望无际的林海。
高原景色,奇丽万状。但也可以简单的用一个“大”字来形容。一块岩石可以有一间、两间甚至三间屋子那样大,而且奇形怪状,自成格局。有的像走兽,有的像飞禽,有的仿佛悬在半空,要立刻压下来似的。令人在下面走过,也不由得要有点儿提心吊胆。
山坡上尽是松、桧、柏和杉树,大的可两三人合抱,树干笔直,好像要刺破青天。树顶相连,枝叶密集,抬头只能望见一线蓝天。几股像飘带似的云雾环绕着山腰,将山峰隔成了几块,只有峰顶突兀地高耸云端。岩石上大都长着斑澜的赫红色、雪青色、或草黄色的鲜苔。斑驳的岩石,加上塔形的松树,绿色的草坪和匹练般的流泉,伊如巨匠挥毫,写出了一幅硕大无朋的山水画!
“大”之外就是“静”听到的只是流泉的呜咽,松风的呼号,兀鹰的饿鸣。这些声音汇成林间的“元籁”听到这些声音,更是令人感到静得出奇,静得可怕。
杨华穿过林海,踏过雪原,在这高原上的柴达木山区,已经走了两天,还没有碰见过一个人!
在静得出奇的林海里,他的心情却是丝毫也不平静。
首先,他是觉得奇怪,为什么走了两天,还没有碰见一个义军?
他看了看金碧漪给他的地图,并没有走错。按说离开义军聚集的中心地点不到百里,已经是应该有义军巡逻的了。“或许是因为树林太大,我一时还未能凑巧碰上吧?”
杨华又想道:“尉迟炯想必早已到了,他会不会跟孟元超谈起碰上我和碧漪的事情呢?”
想起了金碧漪,想起了尉迟炯,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了。
杨华的胸襟并非狭窄,但想起了尉迟炯骂他的那句说话: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”仍是止不住心头的隐痛。虽然尉迟炯在和他交手之后,业已为了这句话向他道歉。
那晚尉迟炯虽然没有明白他说出来,但从他的语气之中,则已显然透露,他是受了江海天之托要给金碧漪做媒的。男的是谁?不用说当然是江海天的第二个儿子,金碧漪的那位江师兄了。
杨华不禁心中苦笑:“江、金两家,门当户对。江大侠的儿子配上金大侠的女儿,那可真是天作之合啊!我算什么?怪不得尉迟炯要骂我是癞蛤蟆了。”
杨华放眼无边的林海,皑皑的雪景,不知怎的,忽地想起金碧漪对他说过一句话:“天地宽广得很,一点无关大局的恩怨,我看也不必老是放在心上。你说是吗?”
是呀,天地宽广得很,他现在是深深体会到了。这无边的林海,这浩瀚的雪原,都可以令人胸襟豁然开阔,在这宽广的天地之中,自己却为着私情苦恼,岂不是太可笑了么?
这句话是金碧漪在小金川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时候说的,当时她说这话,为的是规劝他不要去向孟元超寻仇,而现在杨华却用来自我开解,希望自己能够在相思的苦恼中解脱出来。效果如斯,自是大违金碧漪的初意了。
只须再走几十里路,就可以到达义军的营地了,金碧漪或许见不着,盂元超是一定可以见得着的了!
杨华咬了咬牙,心里想道:“我这一生的不幸,和孟元超有极大的关系,无论如何,我都要弄清楚真相。假如他真的是像爹爹所说的那样坏的人,我拼着受天下英雄暗骂,也一定不能放过了他。”但他却怎想得到杨牧其实不是他的父亲?杨牧编造的谎言,已经深深毒害了他纯洁的心灵。
森林里隐隐传来郁雷也似的轰轰发发的声音,原来是山峰上挂下来的瀑布,从高处奔腾倾泻,冲击两旁的岩石。杨华走到瀑布脚下,看那瀑布在丽日下洒起金色珍珠的泡沫,凉气逼人,不禁精神为之一爽。
他喝了几口凉水,抹了一把脸,心中的尘垢似乎也给这奔腾的瀑布冲洗干净,坐下来略作小休。
忽听得一缕柔和的萧声随风飘来,越来越近。那轰轰发发的瀑布轰鸣,竟是压它不住!
杨华吃了一惊,不但惊奇于吹萧者深厚的内功,更惊奇的是这人所吹的曲调,他好像是什么时候曾经听见过的。萧声柔和悦耳,好听极了。端的有如“间关荤语花底滑,幽咽流泉下水滩!”吹的是江南曲调,好像把人带到了“暮春三月,杂花生树,群蓉乱飞”的江南。
遥远的记忆在心底尚未模糊,山明水秀的江南,杨华也是曾经到过的,不过那时不是茑飞草长的暮春,而是“已凉天气未寒时”的暮秋。
他想起来了,七岁那一年,宋腾霄把他从父亲的“灵堂”之中从他的姑姑手里夺去,带他到江南去找他的母亲。宋腾霄喜欢吹萧,一路之上,就曾不止一次吹过这个曲调。
一个清脆的女声按拍低吟,与萧声相和。
“画船载酒西湖好,急管繁弦,玉盏催传,稳泛平波任醉眠。行云却在行舟下,空水澄钩,俯仰留连,疑是湖中别有天。
“群芳过后西湖好,狼藉残红,飞絮漾壕,垂柳栏杆尽日风,绔歌散尽游人去,始觉春空,垂下帘拢,双燕归来细雨中。”
同样的曲调,前一首是游兴方酣,充满欢乐的气氛;后一首是“群芳过后”则不禁令人有萧瑟之感了。
杨华不懂审音辨律,却也感觉到了乐曲的情绪,不由得暗自想道:“不错这正是宋叔叔当年吹奏过的曲子。但当年是在江南,江南的风景可以西湖作为代表,在江南吹奏吟咏西湖的曲子,那是自然得很。但此处风光却与江南迥异,宋叔叔为什么还是要吹奏这个曲子?”
萧声嘎然而止,那女子道:“霄哥,你还是念念不忘西湖么?”
杨华躲在岩石后,向上望去,只见一男一女,在瀑布的上方,并肩而坐。那中年男子果然是宋腾霄。杨华想道:“这女的想必是他的妻子了。”
杨华猜得不错,这女的是宋腾霄的妻子吕思美。
宋腾霄叹口气道:“是呀,屈指一算,我已经有十二年没有回家了。不知不觉患上了思乡病啦。”
吕思美道:“大哥,我看你不是思乡,你是怀人!”
宋腾霄黯然说道:“不错,我在思乡,也在想起二十年前和元超,紫萝同游西湖的往事,你不会不高兴吧?”
杨华心中一跳:“紫萝?这不是妈的闺名么?”
吕思美叹口气道:“我也十分怀念云姐姐呢,唉,她在小金川的的墓不知能否保全,咱们今年可是不能给她上坟了。”
宋腾霄道:“这你不用担心,元超已经托人照料她的坟墓,那个地方外地人也是不容易找得到的。”
吕思美道:“说起来我是有点担心孟师哥呢,云姐已经死了这么多年,他的伤心依然未过。咱们是怀念好友之情,唉,但在孟师哥,却好像是他也死掉了一半了。”
宋腾霄道:“怪不得孟大哥伤心的,你不知道他们当年是怎样相爱”吕思美道:“我怎么不知道?我也在替孟师哥惋惜呢。唉,这是造化弄人”
宋腾霄叹道:“其实他们后来还是可以成为夫妇的,但紫萝来到了小金川,却不让他知道:“
吕思美道:“那时孟师哥已经有了无双妹子了,我懂得云姐姐的心,她是宁愿牺牲自己,成全别人。”说到这里,勉强笑道:“不过无双妹子也很不错,她和孟师哥配成一对,本来应该是很幸福的。”
宋腾霄道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我不是说林无双比不上云紫萝,而是情天缺陷,纵有女蜗炼石,也难弥补。”吕思美道:“我懂得你的意思,咱们只能希望他在无双妹子的温柔体贴之下,慢慢平复心上的创伤。”
宋腾霄默然无语,缓缓的又吹起萧来。
吕思美道:“可惜孟师哥不在这里,记得从前在小金川的时候,他和我一样,都是喜欢听你吹萧的。”
宋腾霄叹口气道:“过去的事,别提它,我就是怕惹起孟大哥的伤心,不敢在他面前吹萧呢。”
杨华躲在瀑布下面,偷听了他们的谈话,好像是给人在心窝戳了一刀似的不由暗自想道:“难道妈真的是曾经和孟元超做出对不住我爹爹的事情?不,这一定全是孟元超的不对,妈妈不知如何,受了他的哄骗?”
一件事情,最怕知道一些,又不知道一些,杨华目前就是这样。他不敢埋怨母亲,只能迁怒于孟元超了。不仅迁怒于孟元超,连宋腾霄他也有敌意。
杨华在心情激动之下,不知不觉,弄出声响。宋腾霄喝道:“谁在下面?”
杨华站了出来,绕过瀑布,走上山坡。
经过了将近十二年,宋腾霄从少年变成中年,容貌没有多大改变;但一个七岁的小孩,变成了十八九岁的少年,宋腾霄可是认不出他了。
宋腾霄一看,是个陌生少年,而且一看装束,分明不是当地土人,而是外地来的。不禁疑心大起,喝道:“你是谁,为什么跑来这旦?”
杨华心情极是复杂,小时候宋腾霄曾对他很好,他是颇为感激的。但杨牧的谎言在他心里生了根,杨牧说,宋腾霄当年是受孟元超之托,特地把他劫走,为的是用来要挟云紫萝非跟孟元超不可。杨华想起这些奇语,半信半疑,不觉心怀敌意,对宋腾霄怒目而视;宋腾霄道:“咦,我问你,你为何不答,却瞪着眼睛看我?”
杨华说道:“你是什么人,在这里做什么?”依样画葫芦,反问宋腾霄。宋腾霄一听,不觉愕然:“这小子倒像存心和我吵架了。”说道:“咦,是你问我还是我问你?”杨华冷冷说道:“只许你问我吗?”
吕思美道:“大哥不要这样急躁。”回过头来,柔声说道:“我们夫妇二人,是住在这里的。小哥,你好像是外地来的吧。这地方很少人来,所以问一问你。”
她已经说得相当委婉,哪知杨华还是冰冷的面孔,并不答话,又反问道:“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?”
宋腾霄忍不住气上心头,说道:“你问这个干吗?”
杨华说道:“你虽然住在这里,但本来也是从外地搬来的,对不对?”
宋腾霄道:“是又怎样?”
杨华淡淡说道:“没怎么样。既然大家都是外地来的,你们来的,我为什么就不能来?”
吕思美道:“说一说你的姓名,又有什么打紧?”至此,她也不觉起了疑心了。
杨华说道:“我又不想和你们打交道,为什么要告诉你?”
宋腾霄道:“你想和什么人打交道?”面色越来越难看了。杨华比他更不客气,哼了一声,说道:“你管不着!”口中说话,侧目斜瞧,脚步已是向前逼进。
宋腾霄喝道:“给我站住!”杨华说道:“你想怎样?”宋腾霄道:“不说实话,我就和你不客气了!”
杨华冷笑道:“走路你也要管,未免欺人太甚了吧!”
宋腾霄喝道:“少说废话,你跑到这里,到底是要干什么?快说!”
杨华道:“好呀,我还没有见过这样横蛮的人,你不客气,我也不是好欺负!是不是想要打架?来吧!”
宋腾霄又是好气,又是好笑,说道:“你这小子,跑到这里来找人打架,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了,跟我走吧!”身形一掠,已是截住杨华的去路,一抓向他抓下。吕思美忙道:“说不定是个傻小子,大哥,你可别下重手伤他。”
宋腾霄道:“我理会得。”说话之间,五指如钩,已是堪堪抓到了杨华肩头的琵琶骨,试看他是否懂得武功。杨华冷笑道:“你给我抓痒吗?”倏地沉肩缩肘,避招进招,点向宋腾霄脉门。
宋腾霄做梦也想不到,这个看来有点傻里傻气的乡下少年,身手竟是如此矫捷,连忙缩掌变招,以近身缠斗的小擒拿手法,反抓杨华虎口。杨华横掌如刀,顺势就劈下来。这一招有个名堂,叫做“横云断峰”是硬碰硬接的打法。
双掌相交,只听得蓬的一声,宋腾霄连退三步,杨华却只不过是身形一晃。论功力本来是宋腾霄高出杨华,只因他做梦也想不到杨华能有如此本领,出手之时,仅仅用了两分力气,还怕伤了杨华。哪知道就吃了大亏,要不是杨华也没存心伤他,恐怕他的腕骨也要给杨华劈断。
吕思美大吃一惊,叫道:“大哥,你没事吧?这人的确可疑,你用不着手下留情了。”
宋腾霄道:“这还用说,这小子十九是清廷鹰爪。你放心,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,我还会对付不了吗?”
他吃了大亏,下手果然再不留清,说话之间,掌劈指戳,已是接连向杨华攻了十六八招。
杨华以指代剑,以掌作刀,或刺或抹,或劈或按,招数奇幻无比,宋腾霄是个武学的大行家,摸不透他的路数,不由得暗暗惊奇。双方对抢攻势,杨华丝毫也没吃亏。
杨华避实就虚,不与宋腾霄硬拼掌力,宋腾霄自忖,自己分明可以胜得了这个少年的,却是给他弄得无可奈何,不由得渐渐心情暴躁。
转眼过了六七十招,宋腾霄心里想道:“我若是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都打不过,岂不教人笑话?”要知宋腾霄一向心高气傲,虽然此地没有“外人”旁观的只有自己的妻子,他将近百招,仍然未能取胜,也是引以为羞。情急之下,忽用险招。
宋腾霄双掌如飞,倏地滚所而进。这一招也有个名字,叫做“三环套月”招里套招,式中套式,逼得杨华非得硬接不可。
但武学之道,偏攻偏守,都是有利必有弊的。宋腾霄自以为是以己之长攻敌之短,却不料也就着了杨华的道儿。
只听得“蓬”的一掌,这一次是杨华连退了三步了,但宋腾霄虽然站在原地,却是忽然膝盖一麻,身子向前倾仆。幸而他动作得快,手肘支地,立即反弹起来。倘若慢了半分,只怕就要变成滚地葫芦。
原来在那电光石火的刹那,杨华已是点着他膝盖的环跳穴,然后才给他的掌力逼退的。
杨华见他立即就跳起来,不禁心头一凛,想道:“怪不得宋腾霄能够和孟元超并骂齐名,功夫果然了得!”要知杨华刚才虽然不是用重手法点穴,但也不是等闲之辈,立即就可以自行解穴的。杨华自忖就没有这样深厚的内力。
不过杨华心里虽然佩服,嘴上却是“得理不饶人”他一稳住身形,便即冷冷说道:“空手你是打不过我,亮兵刃吧!”他是有意气气宋腾霄,二来也想试试宋腾霄的剑法。由于孟、宋齐名,他试出宋腾霄剑法的深浅,他日和孟元超交手之时,便可以心中有数了。
宋腾霄勃然大怒,侧地拔出剑来,喝道:“好个狂妄的小子,接招!”其实刚才比掌,杨华也给他的掌力震道,双方只能说是打成平手。但他是个成名人物,却怎好和杨华辩论?一口闷气、只能从凌厉的剑招上发泄出来。
杨华待他剑尖堪堪指到面前,这才倏地反击。一招似是而非的“春云乍展”横挥出去,竟然后发先至,避招还招,拿捏时候,妙到毫损。
宋腾霄不禁又吃一惊:“这是什么剑法?”说时迟,那时快,杨华一口气已是攻出连环八剑。从嵩山派的“叠翠浮青”到武当派的“道魂夺命”中间还杂以天山派,峨嵋派、青城派、少林派的各家剑法,每一招剑法都是似是而非,从来宋霄意想不到的方位倏然刺去。
宋腾霄当真不愧是个武学的大行家,虽然不懂无名剑法的奥妙,却也并不慌乱。只见他回剑防身,连退八步,每退一步,就化解杨华的一招,消掉他的一分攻势。不过宋腾霄是当世有数的剑术名家,本来他先发攻敌的,如今却弄得要转为守势,已是感到脸上无光了。
宋腾霄是脸上无光,杨华则是心里暗惊:“他守得这样绵密,我攻不进去。久战定然不是他的对手,须得适可而止了。可是我装作不认识他的,却怎好意思转过弯来?”
剧斗中宋腾霄忽地斜跃数步,喝道:“来者何人?”杨华回头一看,只见一个苗人装束的汉子刚在山腰现出身形。这汉子不是别人,正是他的三师父丹丘生的大仇家,曾经两度和丹丘生争夺石林的那个大魔头阳继孟。
杨华吃惊未过,只见阳继孟的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人,是个年近五旬的妇人。杨华这一惊更甚,原来这个妇人是杨牧的姐姐辣手观音杨大姑。她中年守寡,经常住在娘家,杨华自小就有点怕她的。
阳继孟哈哈笑道:“我只道和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有多厉害,原来连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打不过!”杨大姑则喝道:“宋腾霄,你抢了我的侄儿,还不交给我?”
杨华在宋腾霄跃开的时候,故意装作脚步一个踉跄,趁势抓起一把泥沙,涂污了脸孔,亦是退过一边,靠着大树喘气,好像十分疲倦的样子,话也说不出来。
其卖他用不着涂污面孔,杨大姑也是决计猜想不到,这个和宋腾霄交手的少年,就是她的侄儿。
阳继孟是在两年前看过他的,要是留心察视的话,或许可以认出他来,但此时他也只是奇怪,何以会有一个武功这样高强的少年,并不知道就是杨华。
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小年,能够和宋腾霄差不多打成平手,已经是令得他们惊异不已了。是以杨华装作气喘吁吁力竭精疲的样子,他们倒是认为是必然的结果,确也没有怀疑。
只有宋腾霄自己心里明白,杨华最少还可以和自己斗几百招,杨华自动退过一边,却是令他颇感意外。他本来担心杨华来了帮手,还要和他缠斗的。“难道我看错了人,这少年井非清廷鹰爪?”宋腾霄暗自思想。
宋腾霄松了口气,冷笑说道:“杨华不是你的侄儿!”
杨大姑怒道:“胡说八道,云紫萝这贱人虽然早已给我赶出杨家,她生的儿子可还是杨家的骨肉。我不认云紫萝作弟妇,杨华还是我的侄儿!”
宋腾霄不愿和杨大姑说明真相,哼了一声,说道:“就算杨华是你的侄儿,你也该向段仇世讨还才行。难道你还未知他早已做了点苍双煞的徒弟么?”
杨大姑道:“冤有头,债有主,你从我的手上抢走侄儿,我只能唯你是问!”
宋腾霄冷笑道:“我正想向你们查究那个孩子的下落呢!姓阳的,你到石林向段仇世寻仇,你当我不知道么?段仇世怎么样了?杨华是不是你劫去了?快说!”
阳继孟道:“我和段仇世的梁子与你何关?你硬要为他出头,我也不会怕你!至于那个小子,我要他做什么?”
杨大姑喝道:“丝瓜不要缠在茄子上,我的侄儿下落不明,我只能着落在你的身上!”
宋腾霄情知她是藉口讨还侄儿,特地来和自己生事的,大怒说道:“你这泼妇,简直是无理取闹!要人没有,要算帐就来!”
杨大姑峭声说道:“不错,我正是要和你算帐!”双方剑拔怒张,刚要交手,阳继孟忽地一跃而前,说道:“杨大姑,你要算的是旧帐,旧欠不妨慢慢道讨。宋大侠怪我得罪他的朋友,还是让我和他先算这笔新帐吧!”
十年前杨大姑曾经吃过宋腾霄的亏,如今虽然练成了金刚六阳手的功夫,自忖也是没有必胜把握,于是说道:“新帐要算,旧帐也要算。好在咱们是两个人,他们夫妻也是两个人,两个对两个,公道得很,两笔帐并作一笔算好了。”
吕思美自是不甘示弱,说道:“好,那么咱们男对男,女对女,让我讨教讨教你辣手观音究竟是如何心狠手辣?”杨大姑阴恻恻说道:“讨教二字不敢,嘿嘿,你是孟元超的师妹,宋腾霄的妻子,武功必不差,唯们比划比划!”
宋腾霄喝道:“阳继孟,你远来是客,出招吧!”
阳继孟哈哈一笑,说道:“宋大侠,你怎的这么客气。”宋腾霄只道还有几句客套的说话要交代的,不料他竟是话犹未了,呼的一掌便打过来。阳继孟的“修罗阴煞功”已经练到了第七重,掌力一发,寒随卷地而来。饶是宋腾霄的内功深厚,亦是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颤。
阳继孟心头大喜:“原来宋腾霄不过是浪得虚名。”掌风呼呼,双掌齐发。宋腾霄喝道:“来而不往非礼也,看剑!”剑光霍霍,比阳继孟的出掌更快,阳继孟才发两掌,他已还击三招。攻中有守,每一招都伏下极厉害的后着,登时把阳继孟迫到离身一丈开。身体虽然还感寒意,却也尽可支持得住了。阳继孟的骄狂之气为之一敛,这才知道,宋腾霄并非浪得虚名。原来宋腾霄是因为和杨华先斗了一场,耗了不少真气,功力自是不免打了一点折扣。
杨华靠着大树,自言自语道:“唱戏的哪及看戏的舒服?我乐得躲在一边凉快凉快,看看热闹啦!”
他看了几招,心里想道:“可惜宋腾霄没有一开始就抢先,出剑也嫌还未够快,要破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他恐怕是做不到了。看来“修罗阴煞功”颇耗元气,倘若宋腾霄要是快剑急攻,攻得阳继孟透不过气来,他就不能连续施为了。不过这也怪不得宋腾霄应付不当,一来他的功力打了折扣,二来他是第一次见识“修罗阴煞劝”怎比得上杨华之能知己知彼?
宋腾霄一面要运功抵御寒气,一面要应付敌人的攻击,果然过了不久,便渐渐屈处下风。
另一边,吕思美和杨大姑交手,也是陷于苦斗之中。
金刚六阳手乃是杨家绝技,以掌力刚猛驰誉武林,每一掌劈出,都暗藏着六种不同的奇妙变化。本来这种纯粹的阳刚掌力,是不适宜于女子学的,但杨大姑却别出心裁,另辟蹊径,在原来的家传掌法上又再穷加变化,减少了几分阳刚,加上了几分阴柔,从纯刚的掌力一变而为刚柔兼济的功夫,是以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虽说是继承家业,其中却也有她自己的创造,变得比原来的掌法更为高明,更为阴狠了。
十二年能,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,已经差不多可以和云紫萝打成平手,和宋腾霄拼斗,虽然输了,也不过略逊一筹而已。如今经过了十二年的苦练,金刚六阳手的功夫业已大成,比从前威力更增,也更为无懈可击。
吕思美使的双刀一长一短,长刀用以攻击,短刀用以防身,出自家传,在武林中也是自成一家的刀法。当年她的父亲因材施教,她的师兄孟元超传了快刀绝技,青出于蓝。她是女子,气力较弱,难使快刀。但双刀的招数却是更为繁复奇妙,在防守上也比师兄的单刀更为严密。
不过虽然如此,和杨大姑浸淫了几十年的“金刚六阳手”比起来,毕竟功力还是有所未逮,老练也是有所不如。还幸她的刀法攻守兼施,门户关闭得非常严,苦斗之下,勉强还可支持。
杨华在旁观战,思如潮涌。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师父——段仇世和丹丘生。那日在石林中和阳继孟。洞玄子恶斗,大家都受了重伤,杨华自己也晕了过去。他以为四个人已同归于尽,但醒来之后,敌我两方的四具“尸体”却是都失了踪。这两年来,两个师父生死未之谜始终未解。
“阳继孟这魔头当时所受的伤比二师父三师父更重,他却能够逃出生命,想必我的两位师父也还活在人间?听这魔头的口气,他也似乎未知我的师父是死活?”想起了石林中那笔血债,杨华代师报仇之念自是不禁油然而生,他对宋腾霄不过有恶感而已对阳继孟可是大恨深仇!
跟着想起来的童年事情“妈妈不知受了姑姑多少闲气!爹爹‘出殡’那天!她还冤枉是妈害死爹的,硬要打我的妈妈,如今妈妈虽然死了,她受的气我还是要替她出的。”
宋腾霄恶斗了将近半个时辰,只觉寒意越来越浓,禁不住牙关格格作响。阳继孟得意洋洋,哈哈笑道:“宋大剑客,你还不服气吗?”宋腾霄心高气傲,给他气得七窍生烟,可还当真不敢分神说话。
杨华伸了一个懒腰,忽地走上前来,说道:“可笑啊,可笑!”接连打了三个哈哈。
阳继孟只道他是帮忙自己挪揄对方,心想这个小子倒还知趣,越发得意,便把杨华当作说相声的搭档,有意和他一唱一和,说道:“小兄弟,你说说看,是什么可笑啊?”
杨华缓缓说道:“可笑你太不知自量!”
一盆冷水,兜头淋下,阳继孟笑容顿敛,面色一沉,说道:“我怎么是不知自量?”
杨华说道:“凭你这点功夫,单打独斗,焉能是宋大侠的对手?”阳继孟心想:“莫非他说的乃是反话?”哈哈笑道:“你看清楚没有?我再让你瞧瞧!”连发三掌,把修罗阴煞功发挥得淋漓尽致,宋腾霄止不住连连后退,给他打得手忙脚乱。
杨华冷冷说:道:“不错,你现在是稍占了一点儿上风,可是你们这场架打得太不公道。”
阳继孟道:“单打独斗,有何不公?”
杨华说道:“你刚才不是眼盲吧?你分明看见他已经和我打了一场,你这才来占他的便宜,还能说是公道么?嘿嘿,我都打不过宋大侠,何况是你?假如宋大侠未曾消耗气力,我看你最多不过能够接他三五十招!”
阳继孟见他说的甚是认真,哪里像是在说“反话”?不由得气往上冲,喝道:“好小子,依你说,你是胜过我了?”杨华淡淡说道:“不敢,倘若你我都是一上来就交手,或许你和我不分高下,如今我已养好精神,你是接不了我的十招的了!”
阳继孟大怒喝道:“好吧,那你就上来帮宋腾霄的忙吧,省得我多费气力。”
杨华笑道:“我本来只是想看戏的,可是技痒难熬,说不得也只好再唱一出了。宋大侠,请你让一让场子。要是唱得好,你给个喝彩,要是唱不好,你再替我接场。”
宋胜霄心里猜疑不定,姑且闪过一边,看看杨华弄什么花样。杨华说道:“阳继孟,你数着!”唰的一剑就刺过去。
剑势轻灵翔动,变化奇幻,迅捷无伦。饶是阳继孟在武学上的见识造诣都很不凡,竟也捉摸不定杨华的剑势是刺向何方?吃惊之下,连忙挥袖护身,单掌发出第七童的修罗阴煞功。掌风剑影之中,只听得嗤的一声,白继孟的袖子给削去一幅,化成片片蝴蝶。
杨华冷笑说道:“孟神通当年练到第九重,你如今只练到第七重。修罗阴煞功你练得还未到家呢、焉能奈我何哉?”
杨华一口气喝破他的武功来历不算,而且在一招之内就识穿他的深浅,阳继孟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了:“当今之世,只有我一个人得了孟师祖的真传,这小子年纪轻轻,何以懂得修罗阴煞功的秘奥?真是奇怪!”
宋腾霄在旁观战,也是诧异之极,心里想道:“这少年的剑法或许比我高明,功力分明还是不如我的。我都抵御不了修罗阴煞功的寒气,何以他却居然神色依然难道他刚才对我还是未曾全力的么?”
他们哪里知道,杨华年纪虽小,却是当今正邪两派人物之中,唯一懂得破解修罗阴煞功的人。
原来修罗阴煞功出以归代的武林怪杰乔北溟,乔北溟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,后来成为邪派的首领。张丹枫和乔北溟是同一时代的人物,两人一正一邪。乔北溟是天下第一大魔头,张丹枫是天下第一大剑客,两人数度交手,最后一次,乔北溟终于伤在张丹枫剑下,遁迹海外,不知所终。
张丹枫在他晚年所著的“玄功要诀”之中,记载有破解修罗阴煞功的法门。这部“玄功要诀”和他的“无名剑法”藏于石林剑峰,在三百余年之后,才给杨华发现,孟神通的修罗阴煞功远远不及乔北溟当年,何况是孟禅通的徒孙阳继孟?是以杨华的功力虽然未到一流境界,但用之于抵御阳继孟第七重修罗阴煞功却已是绰绰有余。阳继孟又曾先后两次和杨华的三师父丹丘生在石林交手,因此阳继孟功力的深浅如何,杨华亦是早已知道。
照面一招,杨华就夺得了先手,趁他心虚胆怯之际,立的挥剑如风,着着抢攻。剑势之迅捷雄奇,当真皇有如奔雷骇电。在他怒剑急攻之下,阳继孟已是难以再发修罗阴煞功了。杨华口中念道:“二,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”蓦地一声大喝,收剑凝身,说道:“是不是未满十招?”
只见杨华的剑上有淡淡的血痕,雪地上几点鲜红。原来杨华最后一招,已是把阳继孟的一根指头削掉。只因出剑太快、连宋腾霄都还未曾瞧得清楚。
宋腾霄喝彩道:“妙啊,刚好九招!”至此他已相信杨华确实是有诚意助他,对这少年的本领不禁大为惊异。心里暗暗叫了一声“惭愧”想道:“要是这少年一开始就用全力攻我,只怕我也难免败在他的剑下,但他既然是个侠义道的人物,却不知何故似对我怀有敌意?”
宋腾霄对杨华的本领固然大感惊异,阳继孟给他削掉一根指头更是吓得魄散魂飞。失掉一根指头虽无大碍,但假如不是刚才缩手的快,掌心的劳宫穴只怕也要给杨华的利剑刺穿,修罗阴煞功就要化为乌有了。只削掉一根指头已属不幸中之大幸。阳继孟大惊之下,哪里还有余暇细算杨华用了几招,吓得连忙转身飞跑,唯恨爹娘少生两条腿。
其实杨华虽然懂得破修罗阴煞功,按说也不能在十招之内就把阳继孟打得大败而逃的。只因阳继孟中了他的激将之计,心头动怒,高手比斗,哪容得气躁神浮,这就着了杨华的道儿了。
杨华暗暗叫了一声“侥幸”回头看时,只见杨大姑正在一掌向吕思美击下,用的正是金刚六阳手的杀手绝招。一招六个变式,吕思美难以照应周全,只听得“铛”的一声,左手的短刀已是给她击落。
宋腾霄抢在杨华面前,挥剑如风,一招“李广射石”径刺杨大姑背心的“风府穴”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,尚未沾衣,已是令得杨大姑感到霖森寒意。
杨大姑本想把吕思美抓为人质的,未能成功,哪里还敢恋战?一掌逼退了吕思美,便即斜身窜出。
宋腾霄见妻子没有受伤,放下了心上的石头,大怒喝道:“你这恶婆不是要和我算帐的吗?有胆的你就莫跑!”
杨大姑身似水蛇游走,掠过杨华身边,一掌向他拍下,喝道:“都是你这小子坏了我们的大事!”
杨华想起童年时候,母子受他欺凌,刚才还在自己面前,口口声声骂自己的母亲,不由得也是起了怒气,想道:“你骂我不打紧,骂我亲娘可是不该!”本来不想打他姑姑,此时也非还手不可了。杨大姑的金刚六阳手对付吕思美可以,却怎奈何得了杨华?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,已是给杨华打了一记清脆玲珑的耳光。
说时迟,那时快,宋腾霄已然赶到,叫道:“小兄弟,这恶婆娘让给我吧!”一招“大漠孤烟”剑直如矢,向杨大姑径刺过去。
背腹受敌,这一剑又来得急劲异常,眼看杨大姑已是决计躲闪不开,忽听得“铛”的一声,杨华侧身,放杨大姑过去,平剑当阀,一招“铁锁横江”却挡住了宋腾霄的三尺青锋,缓缓说道:“这婆娘虽然可恶可恨,但也有点可怜,请宋大侠不要和她一般见识,让她去吧!”
杨大姑又急又气,又是大感意外。她外号“辣手观音”平分只有别人怕她,几曾受过人家如此侮辱?杨华这一记耳光,打得她几乎气得发昏,但想不到杨华打了她的耳光,却又救她性命。杨大姑狠狠地瞪了杨华一眼,从缺口便冲出去,转瞬之间,走得无影无踪。
宋腾霄笑道“这恶婆娘似乎还不领你的情呢。”
杨华淡淡说道:“我但求心之所安,本来就不想要她领我的情。”要知他自小就给姑姑的威严镇压,要不是刚才气上头上,他还当真不敢打他姑姑这记耳光,但在这记耳光之后,他的心里却感到莫可名状的痛快!
宋腾霄心中一动,说道:“小兄弟,你可曾学过孟家刀法的么?段仇世是你何人?”
原来杨华刚才要在十招之内打败阳继孟,不知不觉内有几招,已是孟家的快刀刀法化到剑法上来,孟元超把刀谱交给段仇世请他转授杨华的事情,宋腾霄是知的。
杨华情知已经瞒不过去,只好向宋腾霄施了一礼,说道:“宋叔叔,请恕小侄适才无礼。分别多年,小侄不知就是叔叔。多谢宋叔叔问候家师。”他表露了身份,孟家刀法之事却避而不谈。心里想道:“宋腾霄的眼光好厉害,但也怪我学得还未到家,刀法化成剑法,还是露出痕迹。糟糕,要是他说给孟元超知道,我就没有取胜把握。
宋腾霄大喜说道:“原来你果然就是杨华!”高兴之中却也不免有点尴尬。高兴的是好朋友的儿子武艺如此高强;尴尬的是自己竟然败在小辈之手。他的性情和孟元超不同,孟元超是沉稳坚毅,他却比较心高气傲,重视面子。
杨华说道:“不错,小侄正是杨华。”
宋腾霄道“你的二师父呢?你为什么一个人来到这里?”杨华迟疑片刻,说道:“二师父下落未明,我是来找孟元超大侠的!”
宋腾霄怔了一怔,随即面现惊喜之色,说道:“啊,那么你已经知道了?”杨华冷冷说道:“任何事情的真相,总有水落石出之时,不错,我是已经知道了。”
宋腾霄的意思,其实是在探询杨华是否知道自己是孟元超的儿子之事。但在杨华听来,却以为他说的是自己所想象的那个“真相”心里想道:“原来孟元超果然是个坏蛋,哼!”把心一横,跟着想道:“你知道我是来找孟元超报仇,我也不怕!”于是坦然自承,已知真相。
孟元超和云紫萝的一段“孽缘”事关私德,宋腾霄当然不会随便和人说的,盂、云之事,他只曾告诉过妻子,因为他的妻子本来就是孟元超的小师妹。除了妻子之外,即使是义军的领袖冷铁樵和萧志远他也没有告诉。
他正感到难以启齿详告杨华,一听杨华说是“已知真相。”不由得如释重负,大喜说道:“你知道那就好了,那么你自己去找他吧,用不着我多事了。不过”
杨华心里想道:“你当然以为我打不过孟元超,乐得置身事外。好,你不插手,我正是求之不得,”说道:“不过什么?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见孟元超的话,我自己也会找得着他的。用不着叔叔你费心了。”
宋腾霄不觉眉头一皱,暗自想道:“怎么他还是呼名道姓,不肯把元超唤作爹爹?”但随即自己又想出理由来替杨华解释:“哦,对了。年青人面皮嫩,他在父子相认之前,不好意思就唤爹爹。”心想杨华既然目前不好意思认父,自己就暂且当作不知其事吧。于是说道:“不过可惜你来迟了两天,孟大哥已经不在这里了。”
杨华在失望之中,却也不觉的松了口气。原来在他的心底深处,为报私价,要和一个义军的首领拼个死活,他还是感到心灵不安的。虽然这私仇他是决定要报。
“他去了哪儿?”杨华问道。
“三天之前,孟大哥已经去了拉萨了。现在你跟我们去见冷铁樵和萧志远两位头领吧,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。”宋腾霄说道。
到了义军的营地,天色已经大亮。宋腾霄带领杨华走进一个帐幕,冷、萧二人正在和一个中年汉子说话,这中年汉子一见杨华,大喜叫道:“小兄弟,你也来了!冷大哥,萧大哥,这位小兄弟就是、我说的那位曾经帮了咱们大忙的小英雄了!”
原来这个中年汉子不是别人,正是震远镖局的总镖头韩威武。宋腾霄替他们介绍之后,萧志远道:“韩总镖头,这位杨兄弟有件事情,恐怕你还未曾知道呢。”韩威武道:“什么事情?”
萧志远回过头来,笑问杨华:“杨兄弟,前几天你是不是曾经和关东大侠尉迟炯打过一架?”
杨华面上一红,说道:“晚辈不知天高地厚,当时双方稍稍有点误会,晚辈无知,冒犯了关东大侠的虎威。”
萧志远哈哈一笑道:“这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。尉迟大侠说,他平生和人交手,以这一次和你拼斗快刀,最为畅快。他和你不打不成相识,盛赞你英雄了得呢!”
杨华听他口气,尉迟炯似乎未曾把他和金碧漪同在一起的事情说了出来,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,说道:“这是尉迟大侠奖励后进,给晚辈脸上贴金,”
冷铁樵笑道:“当今之世能够和尉迟炯打成平手的,恐怕还没有几个人呢。可惜孟元超不在这里,他的快刀和尉迟炯并驾齐名,要是他在这里,你倒不妨和他比试比试。”
杨华趁机说道:“比试不敢,晚辈只希望能有机会向孟大侠讨教,不知孟大侠去了哪儿。”冷铁樵道:“他和尉迟炯前往拉萨,要是你早来两日,就可见着他们。”
杨华正在有点担心在这里碰见尉迟炯,难免尴尬,听说他也走了,倒是松了口气。但想他和孟元超一起,自己要找孟元超算帐,却是恐怕更加难了。问道:“不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?”
冷铁樵道:“这可说不定。要是他们的事情办得顺利的话,最少也得在半年之后。”
萧志远道:“咱们一面喝酒,一面谈吧。酒席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冷铁樵笑道:“这本来是给韩总镖头准备的饯行酒,现在可又正好可以兼作接风酒了。尉迟炯大侠把碰见你的事情告诉我们之后,我们就料到你会来的,不过却想不到你来的这样快。”
酒过三巡,菜汤两道,喝得兴酣之际,冷铁樵说道:“杨兄弟,咱们虽然是初次见面,你却不是外人。我们这里的事情不必瞒你,你来得不巧,我们这里,目前正是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夕呢。我们已经决定放弃现在的营地,叫兄弟们化整为零,再找隐蔽的地方了。”
杨华说道:“可是已知消息,清兵要来进犯么?”
冷铁樵道:“正是。据我们探到的消息,清廷准备笼络回疆的几个大部落。第一步是叫他们不要供给我们粮食,第二步是利用他们出兵攻打我们。你知道打仗是要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,天时不如地利要紧,地利又不如人和要紧。清兵远道而来,不熟悉地理,当地百姓又不和他们合作,他们是很难‘进袭’我们的,所以必须利用回疆的各部酋长。”
杨华说道:“天下老百姓是一家,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就给清廷利用吧?”萧志远道:“你的话说得不错,不过各部落的酋长却难保不上清廷的当。”冷铁樵接下去道:“所以我们才请尉迟大侠去说服各部酋长,他曾在回疆多年,和许多酋长都有交情。”
萧志远说道:“鄂克沁旗的白教法王是支持咱们的,但白教和黄翰牵涉进西藏的政教之争,在西藏当权的是黄教喇嘛,白教这支喇嘛则在一百年前便已给黄教逐出西藏,如今仍然在青海,不能回去。清廷也想利用黄教来消灭白教。我们叫孟元超到西藏去,就是希望他能够替白教和黄教作鲁仲连的。我们曾经帮忙过西藏喇嘛抵抗天竺外族的入侵,是以和他们两方面都多少有点交情。”杨华想不到这支义军牵涉及这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,暗自想道:“我该留在这里帮忙他们呢,还是到拉萨去找孟元超算帐呢?听他们的说法,尉迟炯虽然是和孟元超结伴同行,但出了青海之后,却还是分头办事的。我可以少了一层顾忌,不过,孟元超办的是大事,我要找他算帐,当然也还得等到他的事情办妥之后。”韩威武道:“可惜我明天就要往鄂克昭盟送药,不能留在这里帮忙你们了。”冷铁樵道:“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,再说我们的目前的问题也并不缺乏人手,而是要打破敌人的阴谋,你不必为了不能留在这里而表遗憾。”这番话给杨华解开了心头的一个结:“如此说来,我留不留在此地倒也无关紧要。”韩威武笑道:“说到帮忙两字,这位杨兄弟才是帮忙咱们最大的人。来,杨兄弟,我敬你一杯。”杨华面都红了,说道:“韩总镖头,你这样客气,我怎么担当得起?其实我也并没有功劳!”
冷铁樵笑道:“韩总襟头并非客气,我也要敬你一杯。你大概还未知道你帮了我们多大的忙吧?我告诉你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