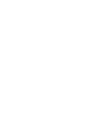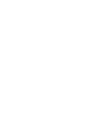我夫君他有病 - 我夫君他有病 第55节
怎么太子妃娘娘开始逼问他了呀,他该怎么办……他能怎么办……
温泠月不知从哪来的一股气,当初大婚那日她没有这么憋闷,在东宫的日日夜夜没有这样委屈,到今天她确实对紫宸殿的一切都厌恶透了。
“你不说话,那本宫便当你无事了,他要吃就吃吧,本宫不伺候了。”说罢,她便撒袖离去,绕过左右为难的嵇白,忽视他在身后阵阵呼喊,一个眼神逼退不知如何是好的侍卫们,又趁着伏青不见了的功夫,扭进幽暗的小道。
离奇的是,素来辨不清方向的她今夜会走得这样顺畅,从紫宸殿出来越过那棵断树再走不久很快就看见熟悉的后门。
“阿颂……”
元如颂素来心性高,她从不难为自己,至于徐衡,只是因为有感情,她才给了他那么多机会。
首先去的就是阿颂府上,若她能安安全全在屋子里便是最好。
乌云层层密布在玉京城中央的天幕,不被人察觉的风搅得黑云袅袅盘旋。玉京空气湿润,连拂下来的风都盈满了水珠才和她脸颊亲吻。
凛冬时节更是化作薄雾,活脱脱像从云上剥离的一朵。
温泠月踏着街口高悬的嫩黄灯笼,对元如颂家是唯一闭着眼,不需要记忆便可走到的地方。
其实她本应去找徐衡当面盘问个通透,到底为什么对阿颂做出这种事。可那小子不知躲到哪去了。
早在很久很久以前,她记得很清楚,徐衡对她说过几句连阿颂都不知情的话。
他说:“小月儿,我去科考的月数里,拜托你多照看阿颂。她脾气烈,又总爱说反话,我不在……她也能少生出些气恼来。”
彼时温泠月只觉得耳朵都快听起茧子了,都是天天待在一块,怎么还要嘱咐起这些来了。何况她们干什么都在一起。
“徐小呆,那你就只说叫我照看阿颂,怎么不关心我啊?”她斜眯起眼,故意揶揄他。
那时的徐衡那张素净的脸腾地红了,他方才交待时说得一本正经,温泠月开口说起时才意识到有多认真。
往事浮现,脚下的步伐愈发快了,直到眼睛可见远处墨笔洒下“元”字的两只大灯笼。
温温的色调高悬在元府正门,一切肃静照旧,门前并无旁人,她心里都是那个盛气的姑娘。
十步、九步、八步、七步、六……
“啊——”
愈发接近阿颂的最后几步,她左臂倏地被身后的一道力拽离原定轨道,身子被那道大力踉跄了几步,连连后退到灯笼稀疏的地界。
那股力的主人始终不曾撒手,她站稳后还稳稳箍住纤细的左臂,指与柔软的绸缎相融。
“你松开我!”
她的声音尖锐,渗透出她被再次打断的不满,正因猜到身后是何人,才有如此态度。
“傅沉砚!”
她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毫无畏惧地吼出他的名讳。
强劲的指骨扣住她蠢蠢欲动的身影,他的脸在背光的高处晦暗不明,他一定看出她的反常,酡红的脸颊如晨醒微弱的焰火,眼深邃似捉摸不透的寒冰。
“那太子妃又是什么意思?”
他话峰急却无不耐,紧紧盯着她欲逃之夭夭的动作。
大抵性格和地位的不等同是他们之间对话的根本错误,温泠月开始奢求小白的出现,甚至这一刻,她认为自己为他挡了那碟杏仁糕点纯粹是她的荒唐之举。
勉强勾起嘴角的温泠月不爽地挤处一丝笑来,“殿下想我是什么意思,我就是什么意思,何况您千辛万苦叫伏青盯着我回去用的晚膳我也吃完了我的部分,殿下现在又在不悦什么呢?”
即便她再多说一句就忍不住要哭了。
傅沉砚一时被气到哑口无言,直到瞥见被他捏住的手腕微微印红,才不自在地松了松,“你就是这样想孤的?你一直都是这样看孤的?”
“你当真那么恨我?”
话出口的瞬间,傅沉砚就后悔了,怎么就将那些话说出来了。
温泠月仰着头,眼眶红彤彤地却不甘示弱地瞪着他,把哽咽憋回嗓中,“殿下何需在意臣妾怎么想,反正您从来没在乎过别人的想法,您顺心才是最要紧的。”
乌云翻滚着北地吹来的风,湿润的空气蔓延,他们的距离或近或远,她难得深藏委屈的模样叫他觉得自己荒唐。
“孤再给你一次机会,最后一次,跟孤回去。”他说话的唇都快要发紧。
少女却固执地紧咬下唇,别过头去,“我要去看阿颂。”
短暂到半分喘息的时刻,他终于开了口:
“好!好!”紧箍的手腕彻底松开,他接连后退两三步,“温泠月,你说得很好!”
“待会淋成落汤鸡,湿漉漉地踏进东宫的大门!”
她没有转头看他,听见的只有离开的脚步声和他那驾檀色马车卷尘驶去的声音。
大抵是松了一口气,停顿在原地抬手拭去被吓出来的泪珠。
傅沉砚的举动她越来越无法理解,可细想,他本身就是一个叫人捉摸不透的人。
云层浓厚如墨,大抵不足一刻钟却是有一场雨要砸下来。
她形单影只地跑出来,却是没有考虑到任何,下定决心迈开踏入元府。
隆重浩大的车轱辘声比闷雷还嘈杂,身后薄风掠过,她在回头的瞬间被那个淡淡的雪松香施力抱起,扛到肩上,不顾她回神后的打闹叫喊,阴鸷清冷道:
“在孤面前,没得选择。”
--------------------
第48章 第四十八颗杏仁
“傅沉砚你放肆……”她在他肩上一刻不得安宁,挣扎着想要逃脱桎梏,却不得而终,被傅沉砚一股脑塞入马车里。
一阵嘈杂交织着她的不甘,珠玉帘碰撞,天际滚动厚重的乌云,几乎在她被傅沉砚抱入马车的瞬间,细密深重的雨点纷繁落下。
交融着一切声音。
而傅沉砚脊背已然被淋了湿润。
那少女种种情绪涌上心头,瞧着傅沉砚沉色定定坐在门旁,已然不悦,不会为任何言语劝阻所动。
“傅沉砚……”
什么太子,什么殿下,他不是小白,也不是什么好脾气。
温泠月有时候觉得自己特没面子,明明那么生气了,明明那么讨厌他,明明下定决心不再理他。
可真到了面对面的时候,她气急,还是忍不住掉眼泪。
“别哭了。”
傅沉砚紧咬牙关,没有去看她,也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辞,手却诚实地捏着一块柔软的绢布,状似无意地触及她划着泪珠的侧颜。
温热的泪水刚一触上细腻的绢布,那一角陡然被浸湿。
他似乎意识到什么,沉而轻快地吐出一口气,怨怼自己,也怨那双不听话的手。故而将手绢丢入她手里后便不再动作。
手绢还停留着那人身上残余的温度,和细细收藏在怀中沾染的雪松香。
一路寂静,唯余碎玉坠地的雨声响彻在耳畔,珠帘之外是可见的雾气在迸起的水珠中袅袅,东宫都被雨水敲打出一层模糊的外壳。
她的泪不知是在何时止住的,只是掌心绢布的温度,让她静静凝视窗外,不再作声。
坐下两人后略显狭窄的马车里,二人间不过短短几拳的距离,却容纳了世间最寂静的情绪。
大抵是他的到来将那阵诡谲的氛围带到了东宫,温泠月回福瑜宫后趴在窗沿,任由南玉几番呼唤也没有一星半点的回应。
阿颂的情况是她最担忧的,但现下却无济于事。
“娘娘,您把身上的湿了的衣服换下来吧,或者让我帮您擦干些也好啊。”
南玉望着身上因方才回宫弄湿的温泠月,又看了看床上摆着的干净衣服,却等不来她的答复。
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眠不休地下了三个时辰,她一夜未睡,直到……
将近寅时一刻,福瑜宫院里多出了一个高大的阴影。
彼时南玉和院中一众婢女下人昏昏欲睡,他未撑伞,踩着雨和水洼,向她的窗边步来。
没人能懂温泠月的小众爱好。
她趴在窗边,支开那扇贴了花的窗户,不顾雨水顺着倾斜的窗面滑落,滴到窗沿的枯枝上,再星星点点溅在她脸上。
无人察觉男人的靠近,直到他靠在她栖息的窗外,屋檐垂下一道雨幕,作为他短暂避雨之地,而他侧过脸以目光勾勒着姑娘的模样。
“你就那么在意徐衡和元姑娘的事?”
他站定良久才开口。
他知道她没睡着。
温泠月一哆嗦,刚想开口说什么,却不由自主被冻得打了个喷嚏。
“阿颂他们二人都是我从小一同长大的朋友,明明连婚帖都下了,阿颂还答应让我坐在最好的那桌吃,结果现在徐衡居然……”
她气不打一处来,越说越激动,愤愤地抬手拍在窗沿木板上,却意外激起一滩小水洼,水珠悉数打在傅沉砚脸上。
“那小子居然敢私通!”
语毕,她才注意到被溅上一脸水面容不善的傅沉砚,下意识噤声,气息微弱了些。
好在他没有过多追究什么,只是说:“你口口声声说你们三人一起长大,可你对他们究竟有多少了解?”
这话叫她怔愣了一瞬,“我当然了解他们了。”
“阿颂她虽然胆子大,看着像什么都不怕,说着什么都不在乎的话,但其实……她心最软了。”温泠月默默细数她的阿颂,又说:
“徐衡啊,从小就是块不通人情只会死读书的木头,还总被阿颂欺负也不知道说。我本以为他那个书呆子一样的性子这辈子都讨不到老婆了,谁知他福分大,能娶到阿颂这样的妻,结果还被他……”
想到阿颂现在承受了多大的委屈,温泠月就说不出话来。
少女喋喋不休了许旧,她似乎从未在傅沉砚面前说上这么多话,以这样随意的姿态。而那个素日耐心有限,闲心不足的太子殿下,就这样同她待在一个僻静的地方,听这个姑娘的碎碎念。
她说得口干舌燥,却不觉得累,似乎细数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刻总是很开心。直到那个沉默良久的傅沉砚忽然开口说:“那你知道,你口口声声最了解的朋友,究竟想的是什么吗?”
“什么意思?”
傅沉砚扭过身子,呈面对着她的模样,他身后雨幕模糊,意外拍落在肩头的雨水却清晰,而他的面容也全然映在她瞳孔中。
只听得他一字一句说了什么,令温泠月整个人不由自主地正了正身子。
从他口中说出的,是她从未想过的事态发展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